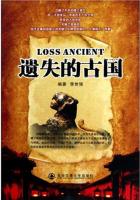天色暗沉的厉害,远方的天边显出一抹奇异的青蓝色,不过才数个时辰,那积雪便已经没过脚踝。
绫月城在雪地里快步的行走着,棕褐色的鹿皮短靴在那雪地里浮浮沉沉,鞋底沾染了雪屑,渐渐有些举步维艰起来。
碧涯举着伞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然而腿总归是短了一截,手上又拿着托盘,不知不觉的落在了后边。
这雪越下越大,隐隐有淹没天地的气势,那纷繁的雪花迷乱了双眼,四周围的一切都变的陌生而茫然。
这后花园平日里是走过千百遍的,今日不知怎么的总也走不到头,脚步踩在地上,顷刻间就被隐没了,了无痕迹,仿佛他这个人从不曾出现在这世上,也不曾走在这世间走过一遭。
他抱着斗篷无措的站在雪地里,四周白茫茫一片。
雪片是未曾见过的大,似一片片羽毛,自九天之上翩然而下。从前他总以为那鹅毛大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今看来却是所言非虚了。
他下意识伸手去接,那雪飘飘然落于手心,凉的他一下将手缩了回来——好似那不过一瞬的触碰便感到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凉。
他赶忙将手缩进袖子里,视线中忽然出现一抹奇异的红色。起先只是零星一点,渐渐的纷扬乱舞起来,他惊诧的抬头,却见那漫天飞雪都的透出血色的光华。水红色的雪絮绵延千里,仿若彼岸荼蘼花事了……
空气里骤然泛起水红色的烟雾,如奔腾的潮水朝着他的脚下袭来!他痴痴的望着那汹涌的血雾,突然觉得有些怕。
九州奇幻录有记:一年冬之初,雪之始,常有雪魅出没,见落单之人便以雪雾迷惑对方……
难道不成——自己是遇到妖怪了?
这个心思在绫月城心头一转,便有些的慌乱了起来,他在雪地里团团的转,然而往哪里走都是一样的。
雪,铺天盖地的雪,无处不在的雪。
血雾弥漫,诡异而又美丽。
这些东西就这么不想放过他吗?绫月城有些懊恼的想,耳边却恍惚听见一阵女子银铃般的娇笑,风一般在他耳畔掠过,仿佛近在耳前却又远在天边。
“好冷啊……”
“真的好冷啊……”
那声音过于哀怨,似有一股寒气直击人的灵魂,绫月城只觉头皮一阵发麻,眼前似乎有一道道人影来回飘动,无数的声音在他耳侧盘桓,偏他定神去看时却有无论如何也看不透彻,好似眼前蒙了一块白纱,幻影朦胧,令人眼花缭乱。
他早知自己双眼有异,能窥见非人的事物,但总没今日来的真切,到如今才真正觉得,有些宿命是逃不脱的。
那雪魅之音声声惑人,他想逃离,脚下却似有千斤重,明明该是惊恐万分的大叫,却不自觉的走神了。
他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天,也是一日初雪,有个云游的和尚途经侯府。
那人不要金银,不要斋饭,却偏说在侯府上空看到异光,强行闯入府中,说来也怪,他那样弱不禁风的一个人,府中护院家将竟无一人能阻拦他。那时他尚且年幼,正随嬷嬷在后花园散步,猛然间见到一个和尚闯到眼前,吓的躲在嬷嬷身后不敢出声。
说是和尚其实不大像,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瘦瘦高高,光溜溜一颗脑袋点了九个戒疤。穿的却是一身袈裟却是极风流的大红色,松松垮垮的披在身上,手掌上缠一串不知材质的碧色琉璃念珠,一双细长桃花眼里皆是让人惊疑的坏笑。
他擅自抓住绫月城的肩膀,全不顾嬷嬷在旁惊呼大叫,一把将他拽了出来,动作粗鲁毫无章法,笑着道:“这位小公子端的是相貌不凡,骨骼清奇,然而眉眼带煞,命途多舛,不若拜我为师随我修行,否则一生磨难数不尽怕是活不过十八岁。”
这嘴可够毒的,一开口便是咒人短命。
老侯爷哪里肯依?命府中护卫抓捕他,可那和尚不知施了什么妖法,挪移腾转,上蹿下跳,竟无人能奈何得了他,后来还是央了公干到此的大将军沈獠,借了兵才将那和尚打了出去。
可也不知是凑巧还是命中注定,那之后绫月城便大病一场,至此每日药不离身病怏怏到如今。细细想来,那和尚说的也不无几分道理,不要说他这病体能不能拖到十八岁,就是今日之劫也是生死难料。
“呵……”思及此他忍不住笑了出来,然而立刻就闭上了嘴巴,那笑声低哑难听,无边的雪地里让人毛骨悚然。他盯着那一无所有的雪地看了一会,忽然的冷静了下来。
若他真该命丧于此,也好过每日里喝那些药汤生不如死,索性坐了下来,一动也不想动了。
他裹的大氅乃是当今圣上御赐,整只北地巨熊的皮毛所做,覆在身上寒气丝毫不能入侵。雪地松软,四周静谧,竟然是难得的舒适,绫月城打了个哈欠,坐在雪地里睡着了。他想若是真要结束这一生,就此睡去也是极好的,那些雪魅的声音反反复复在周围徘徊,初时乱人心神,最终都远去不可闻了。
梦中似乎有人在哭泣,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里,四处都是僵硬冰冷的尸体,有的被野狗乌鸦挖开了腹腔,露出内里鲜红的脏器与森然的白骨。一人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脸深深的埋在雪里,身子不由自主的抖做一团,她瑟缩着道:“公子,我饿啊……”
绫月城抬手想去触碰他,却见她忽然的转过身来,一层灰色的薄膜裹着削瘦的脸颊,双眸因为过度的凹陷形成而变成两个黑洞,嘴唇干瘪,哪里是什么柔弱的女子,分明是一具瘦骨嶙峋的骷髅罢了!只见她纤纤的指骨猛然的扣住绫月城的手腕,将他的手往嘴里塞,一边塞还一边哭号着:“我好饿啊……我好饿啊……”
竟是要硬生生的将他这个吞进肚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