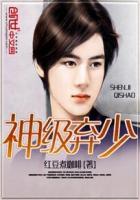“二婶,我是来道歉的。”巩雪把梳子轻缓地放在旁边的小柜上,面色平静地向张素琴道歉。
张素琴的脸在灯光下发出青黑的颜色,一双刁钻精明的眼睛忽闪忽闪,神色间阴晴不定。巩明军比妻子好不到哪里去,看到巩雪的时候,他难堪又羞恼地低下头。
张素琴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哟,我哪儿敢受咱们家千金大小姐的道歉啊!明军,你说是不是,我们还是夹起尾巴做人比较识趣!”
巩明军的眼皮闭了两闭,声调极冷地对巩雪说:“没事就出去吧,我们也该休息了。”被妻子辱骂已经够丢人了,他不想再被亲侄女瞧不起。
巩雪把一支治疗外伤的药膏放在梳子旁边,语气淡淡地说:“二婶,这是治疗抓伤的药膏,很管用的,你用用试试,要是还不好的话,我陪您去医院。”
张素琴冷哼了声,脸上被阿原抓伤的地方不可抑制地抽搐了两下,“算了吧。要是把你再牵扯进来,老爷子又会骂我影响你学习了,唉……我就是苦命人啊,受了伤,没人心疼不说,还得自己个搭上医药费!”
巩雪露齿一笑,实则是冷笑,“医药费大概是多少?”
张素琴眼睛一亮,不过又装模做样地摸着她刚刚做好的指甲,漫不经心地说:“怎么的也得两三千吧……这可是脸,脸你懂吗?女人的脸,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宝物,一不留神被伤着了,那可就变成烂泥一样一文不值了。”
巩雪点点头,湖水般的黑瞳眨了眨,说了句稍等,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很快,她拿了一沓子纸钞进来,还放在梳子的旁边,“二婶,这是三千块钱,您拿去看病吧。就当是我为阿原赔罪,您要快点好起来,省得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脸,变成烂泥巴就可惜了。”
张素琴见有钱拿,才不管巩雪其实借机暗讽她呢。金子变成烂泥巴,有钱花,也是金子一样的烂泥巴不是……
她的脸立刻阴转晴,几步便走到门口,抢似的把钞票抢在手里,笑得春花一样灿烂,“就知道小雪最义气了,老爷子都及不上……”她想说老爷子都及不上你大方,可是后几个字没说出口,就被巩雪清冷冷的视线逼退了回去。
用世上最俗气也最有效的办法解决了二叔二婶,巩雪稍稍松了口气,她用钱想买的是家里的平静和爷爷身体的康健,只有爷爷舒心了,她才有信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洗完澡,又温习了今天考试的内容,时间已经接近凌晨。她躺在床上,把毯子掀开一角,阿原立刻很有眼力见地蹦上来,躺在她的身边。
她俯下身,亲了亲阿原长长的胡须,笑着说:“晚安,阿原!”
“喵……”
关灯的时候,她又看到了桌上的手机。想到高原的叮咛,她又坐起来,给高烈打电话。
记得他们最后一次通话,还是在南疆的家属房里。那个时候,他言语非常不客气地警告她,不要毁了高原的前途,更不要肖想她能走进高家。生平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那样叱责,说不屈辱,不伤心是假的,从那以后,她便有了心结,不想和这个言语犀利冷漠的军官再有任何的牵扯,她知道他同样不想,因为她违背了诺言,没有离开高原……
没想到拨了那么多次都不通的电话,却在这个时间一下子通了。
接通的刹那,巩雪的手心紧张得冒汗,而她怀里的阿原,竟然先她一步,冲着手机喵了过去……
“喵……”
巩雪的头嗡的一声轰响,紧接着,她用手盖住阿原极度热情的嘴脸。
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敢胡乱招呼!
那边显然也被这个喵星人的电话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静了静,巩雪忽然听到一声低哑的,犹如山谷中传来的回声:“喂。”
巩雪怔了怔,怀疑她是不是拨错了号码。
这声音……
和记忆中那道冷漠犀利的嗓音,怎么差那么远呢?如果那道嗓音是滴水成冰的莽莽覆雪山峰,那么,现在她听到的这个声音便是沉静沧桑的幽幽远古潭水。
古井般的沁凉无波的嗓音,不知怎么的,让巩雪的心头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奇怪感觉。
她闭了闭黑瞳,提着一口气,对着话筒说:“你好,我是巩雪。请问,你是高烈吗?”
对方清晰而又略显粗重的呼吸声透过几千公里的电波,传进她的耳廓,寂静的夜里,隐隐漂浮着一丝不安和忐忑。
张张嘴,却听到对方清淡沉静的回声:“哦,是你,我是高烈。”
巩雪捏紧话筒,目光紧张地盯着台灯的按钮,“哦……高原……是高原让我通知你,记得给你的妻子回个电话,她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找你……请……”她忽然察觉到一丝异样,打住话 等了有十几秒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才哑着嗓子,忽然笑了,笑声很短,几乎是一掠而过,可她却微微一颤,第一时间感觉到那声笑里隐隐透出的嘲讽意味。
“你也和阿原一样,笑我识人不清?”高烈没头没脑的问话,一下子把巩雪问懵了。
什么识人不清,和高原又有什么关系?
她不想跟高烈谈下去了,她找他没别的目的,只是充当传话筒的角色,并不想掺和他的家事。
可让巩雪没想到的是,现在的高烈并不是正常人,他身体内的酒精浓度,至少要在200mg/100ml以上。
而致使他醉酒的那个人,正是通过巩雪找到他,请他务必回电话的妻子,冯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