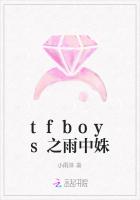我将脸稍稍往右边侧了点,清晰地看见房间的右面墙上的那只钟,它告诉我现在是10点50分。我终于明白了,我是在进行第二次乳房手术。“10点50分”,太好了!这个时间告诉我,我的左侧乳房肿瘤肯定是良性的!因为我第一次右侧乳腺癌的手术时间是5个多小时,要到下午1点半才苏醒的。能有这样的逻辑推理,说明我已经比刚才清醒多了。
“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有没有医生和护士?”我看见有一位穿白大褂的正往我这边走来,也许她看见了我的脸在动。
“林医生。”我认出来了,她就是我两个月前右侧乳房手术时的麻醉师。
“你怎么又来了?”她也认出我了。
“我左侧乳房又不好了。”我说着嘴里就感觉有异物,想吐,她赶紧用毛巾垫在我的右腮边,我一边吐一边又无意识了……
确认这是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时,我终于彻底清醒了。
刚才那一幕,太恐怖了!我之所以没有被吓死,是当时的身体不具备“害怕”的能力。
护士小姐来帮我测量血压。她告诉我,我刚才是在苏醒室,而我右侧乳房手术时并没享有此待遇,因为那天该手术室只有我一台手术,所以我是在手术室内苏醒的。
这是我在短短的5个月内的第三次全身麻醉,挨的第三大刀。这次手术前,担心的是自己患了双侧乳腺癌。而现在的结果是良性肿瘤,但这个好消息却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医生根据我左侧乳房的乳腺质量和导管内的乳头状瘤的程度,最后还是采取了全切除。
我终于成了一个“零乳房”的女人!按理说,术前我有“全切除”的思想准备。但当自己真的面对活生生的事实时,心里却又“理性”不了了。
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是什么女人?
就一个字:惨!
第二天早上,医生来检查伤口,换纱布。
解开胸前的绑带,撕开伤口的纱布,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酒精棉球擦拭着近20厘米长的伤口。此时,我用眼睛证实了一下现实,“乳房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伤口很好,安心休养。”医生干完他的事,嘱咐一句,离开了病房。
病房恢复了安静。安静的病房让我安静地思和想……
一个男人的身边,如果躺着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而且是一个胸前卧着两条“铁轨”的无乳房的女人,这个男人会怎么想?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男人。
患了癌症而其配偶或恋人提出分手的,为什么是乳腺癌患者居榜首?理由还需要说明吗?
不要这样狭隘地去评判男人,或许男人有更充分的必要理由!
给点理解吧,特别是当自己已经走在人生边缘上的时候。
其实,在我的信息库中储存着两个非常感人的版本。
一个是美国青年版本:
这是两个美国人,男的叫肯·威尔伯,女的叫崔雅。我记得崔雅是在她36岁时相识了肯。于是,双方一见钟情。2周后求婚,4个月后结婚。但就在婚礼前夕,崔雅却发现患了乳腺癌。
崔雅问肯对她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肯非常坦诚地告诉她:这当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我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
此时的崔雅对完全可以马上转身的丈夫的诚挚之语,内心还是充满了担忧:残缺不全、瘢痕累累、左右不均的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
也就在此时,肯突然调整刚才那种信誓旦旦的风格,说: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享受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的日子我有幸与你那超丰满、超性感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
崔雅笑了。
肯继续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有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
这时的崔雅,像条蚕,蜷在丈夫的怀里,肯热烈地用双臂揉抱着崔雅,两人对视得甜甜蜜蜜,而后笑得眼泪直流。
接下来的日子是完全出乎两个人的意料的。
5年里,崔雅由右侧乳房肿瘤,逐步扩散至左侧乳房,最后是脑部和肺部转移、恶化,终而不治。那天,肯是让崔雅躺在自己的怀里走的。
在这些煎熬的日子里,肯践行着对爱的许诺,自始至终陪伴着妻子走过那漫长的苦厄。崔雅的身体虽受尽折磨,而心却能自在、愉悦,因为有肯的滋润和磁场。他俩谱写了这个时代已少有的爱情诗篇。
送走了崔雅,肯·威尔伯干了一件事:将妻子的婚后日记,更确切地说是妻子病后的日记,加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就了一本名为Grace and Grit(《恩宠与勇气》)的书。书一面市,就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
第二个是龙的传人版本:
这是一个老华侨和大陆妹的故事。几代人旅居新加坡的华人许先生,花甲之年成了单身。于是,他在网上“海选”伴侣。当鼠标点击在中国杭州的一位女士的照片时,许先生定格了:就是她,很“东方”啊!
她叫莉莉,一位中学英语教师。2001年患了乳腺癌,再婚的丈夫在她术后的8个月不辞而别,回他原来的家了。莉莉擦干了眼泪,埋葬好旧情,回到了三尺讲台。5年后的今天,她退休了。找个伴侣,是她现在的功课。许先生的照片,她看了看,觉得不仅顺眼,还有点儒雅;工程师的阅历,也合她心意;再接下来就是年龄,长8岁嘛,符合再婚的年龄差。
走完网上相亲的硬件程序,他俩开始“e-mail”。
键盘敲完几个来回后,莉莉突然发现,许先生更适合她的一位女朋友琴琴。因为莉莉一心想找个母语为英语的伴侣,那她的满腹英文就有用武之地了。
而琴琴小莉莉5岁,她单身不久,长得也“东方”。机械设计专业的大学教师。但英语是她的“短板”,所以,只会用英语沟通的男士,自然不在她的视线内。而同专业会中文的许先生,她认为不错。
在网上,许先生和琴琴谈了10天朋友,最后,以许先生的一句“还是让我回到莉莉身边吧!”宣告恋爱终止。
莉莉对许先生说,琴琴比我年轻,大学教师比中学教师知识博,同专业的人共同语言多,特别是她双乳齐全、身材好等等,讲了一大箩筐琴琴的优势,可许先生仍旧“我自岿然不动”!甚至许先生正面回应了莉莉的乳房爱情学说,明确表示:“一只够了!”
许先生飞到杭州,在莉莉家对面的宾馆里住下了。
莉莉有点感动。
他放弃在99个正常人中作选择,而独独咬定我1个非常人不放松。
她彻底感动了,缘分啊!
婚后,莉莉随丈夫回新加坡定居。许先生和莉莉成了华人圈内的模范伉俪。
当然,过日子哪会天天是晴天,有阴天,也有雨天。但雨过天晴,彩虹却更美了。
这两个版本,各有各的情节:
肯·威尔伯和崔雅,相识4个月就完了婚,这样的“闪婚”照样能让人爱得荡气回肠,爱得毫无功利。
许先生和莉莉,是传统的“看照片”+现代的“e-mail”而后进了“城”,这种在虚拟世界里的网恋照样能让人爱得实实在在,爱得真真切切。
版本虽有不同,真理却只有一个:
爱情不仅超越乳房,超越时间和空间,更超越死亡!
肯·威尔伯们和许先生们,在人间。
“潘老师,这是黑鱼汤,医院食堂的清汤不要吃了,长不好伤口的。”中午开饭时,11床的丈夫又给我送汤了。
“谢谢,太不好意思了。”我歉意地说。
11床和我一样,右侧乳腺癌。可13年后的今天,她的左侧乳房居然还会Copy不走样,无奈啊,上周也做了全乳切除术,和我一样成了“零乳房”女人。她丈夫每天认真地变换着花样给她送汤,她却嘱咐丈夫给我也送一份。同病相怜啊!
午休的病房静悄悄。静悄悄的病房我却毫无睡意。因为我想她了——我的那对乳房。
她是我永远失去了的东西,追思是免不了的。
她,陪伴了我整整55年。
她,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痛苦。
让我真正感觉到她的存在是我14岁那年,小学6年级。我发现自己平整的胸部开始突起,越来越突起,像两只“生煎馒头”。那年夏天,被妈妈发现了。她说,“你应该穿件贴身的汗衫马甲,要不然太难看了。”随后,我听见妈妈轻轻地说了一句“小姑娘,开始发育了”。
60年代的14岁其实只有现在10岁的智商,什么是发育?不知道。而妈妈的话,让我明白:我需要遮丑。穿什么样布料的衣服能遮丑呢?
那个年代有两种布料很受欢迎:的确良和人造棉。的确良很薄,却很挺,不易皱,但我不喜欢。因为它很透明。里面是戴胸罩还是穿马甲,抑或什么都没穿,外人一目了然。再说的确良价格特贵,妈妈也不会给我买的。
而人造棉虽然比的确良价格便宜多,而且也不那么透,但穿在身上太贴身,减不了我那两只“生煎馒头”的高度,就是遮不了丑。相比较不太贴身的布料就是棉布。穿棉布衣服不太透明,又不太贴身,还可以免去穿汗衫马甲。夏天,少穿一件总比多穿一件好吧!
让我又一次感觉到她的存在是我19岁那年,刚进工厂接受再教育。我发现自己那两只“生煎馒头”已经悄悄长成了“高庄馒头”了。有趣的是,我不再认为是丑,而认为我比胸部平平的小姑娘要好看。特别在夏天,我戴着自己做的布胸罩,穿上连衣裙,再着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头上戴着一顶别着一朵小红花的草帽,上下班进出厂门口时,蛮得意的。
后来,同厂的一位小姐妹与厂里的男青年谈朋友,她告诉我,那些男青年背地里称我为“挺挺”,说我走路很挺的。我想,恐怕不是因为我的腿吧,实乃是因为我的胸吧!精确地说,是我胸部的乳房挺吧!我觉得这些人真无聊,思想很“下流”。这就是当时文革时代的评判标准。
让我刻骨铭心地感觉到她的存在是我23岁那年,乳房患了小疾,并动了个小手术。那时,我学徒满师已经1年多了。一同进厂的许多女孩都有男朋友了。我那位8级车工的师傅开始为我物色男朋友。
师傅说,钳工组的小张人不错,长得也端正。你俩谈谈看?
师命难违,我答应了。
我和小张谈得一路顺风顺水,我家人也很欢迎他。
正准备着去他家亮相时,突然,叫我到弄堂口电话房去接一个传呼电话,是小张妈打来的。她大声地明确告诉我,她坚决不同意我与她儿子谈朋友。还说了很多话,我当时都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一句。
回到家,小张已经坐在我屋里了。
“我刚在家与妈妈大吵一顿,她不同意我俩好。还说她要立即亲口对你讲,我就赶来了。”他紧赶慢赶,还是赶不上他妈妈的速度,让我先于一步听到这恐怖的结论。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他。
“因为你乳房开过刀,以后会生癌的!”
“我是良性的,乳房纤维瘤,不信,可以去问医生!”我委屈地大哭。
“你妈怎么知道我乳房开过刀?”
“车间里的小王告诉她的。”原来,他妈妈向厂里其他人打听我的情况时,顺便了解到的。
“我妈还说……否则……与我一刀两断!”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这句最后通牒,但小张坚决表示不会因此变心,大不了不回家了。
我经过几天苦苦地思索,实在不愿意让他选了老婆扔了娘,娘是不应该被不选择的。
唯一的办法:我忍痛割爱!
这都是乳房惹的祸!
现在想来,如果我当初,能从此将张妈妈的话当“最高指示”来遵守,天天呵护好自己的乳房,也许今天就不会“中彩”了。
在25岁时,我开始进入女人的又一大程序:恋爱、结婚、生子。在这些程序中,我的那对乳房,除了让我体会到在“性”福时对男人的蛊惑作用外,更让我体会到初为人母的无比自豪。当儿子在我的怀中,闭着眼睛,本能地张开小小的嘴巴,第一口吸吮我的乳汁时,一股痛的愉悦让两个生命爱成一体。其实,这才是乳房最原始,也是最崇高的功能。
在我45岁至55岁的这10年,我的一对乳房真是给我撑足了面子。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体型往往会任着性子变化:腰,争着和上下腹部连成一体,有时臀部也要挤进来,于是大家实实在在地成一“桶”。最讨厌的是乳房,偏偏在此时也“怠工”了,懒懒的,提不起精神,渐渐往下垂。
而这时的我,仍旧该突的突,该凹的凹:胃是胃,腰是腰;臀部照样恪守其职;特别是乳房,在她的岗位上精神焕发,坚挺依旧。
我,太不合群了!遭到了周围许多女朋友的妒忌:“美死你了,什么衣服都能穿!”
最有趣的是我到胸罩店买胸罩,那些营业员小姐边帮我量尺寸边尖叫:“70C罩,不得了,模特儿身材!”
70是胸围的尺寸;C是罩面的大小。这是我25岁时的尺寸,55岁的我仍旧30年一贯制。当然,我不能贪天功为己功,这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而是老爸基因的功劳,我奶奶活到79岁,照样是老年模特身材。
有一位男人,白底黑字,很文学地描绘过我的乳房。享有这一权利的,当然非我丈夫莫属。一次,他兴致勃勃地朗读给我听,我听得肉麻肉麻的。此时,可能无声的视觉阅读要强于有声的听觉语言。
别了,我那可爱的乳房!
别了,我那恐怖的乳房!
有了,我那让我永远坚挺的义乳!
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中国哲人老子曰: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
中国女人潘肖珏曰: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气馁;否极,还会泰来。
病房里嘈杂起来了。
到了护士开始量体温、问病人的两便情况的时候了。我的乳房追思会结束。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交给医生,但不完全交给医生。
学做聪明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