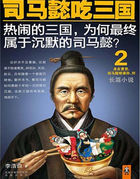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那个被判罚走亿万兆公里的犯人站着看了很长时间,便躺在路边,道:‘我不想离开,这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因此不离开!’用一位有教养的俄国无神论者的魂魄和在鱼肚之中生了三天三夜闷气的预诸约拿的魂魄混在一块儿,——就是这个横卧在路上的思想家的品格。”
“他躺倒是否因为有东西作铺垫?”
“在那边一定有东西垫。难道你是在哭?”
“太棒了!”伊万赞赏地说着,他仍令人费解地兴高采烈。现在他带着突如其来的好奇心听得十分有味儿。“难道你还躺在那儿?”
“问题最重要就在于他现在没有继续躺下。他好像躺了一千年那么久,现在终于站起来开始走了。”
“真是笨蛋一个!”伊万哈哈大笑,就像精神病人一样,但心里却同时在算计着什么,“一直躺着和徒步走亿万兆公里路还不都是一样的吗?这段路估计得走十亿年。”
“根本不止,如果现在有纸和笔,一定可以计算出来,但他早就到达了,因此引发了这段笑话。”
“不太可能吧!他哪有十亿年的时间呢?”
“你老想现在存在的地球!但你要弄清楚,现在的地球本身也许经历过十亿次反复的变迁;后渐渐冰封、老化、开裂、粉碎、分解为各种元素,又变为天空以外的水,然后又出现了彗星、太阳、地球——就像这样反复无数次的循环,而且从头至尾是用一种方法,丝毫不差。实在无味的要命……”
“那么他走到了又如何?”“天堂之门刚为他打开,他踏过去,还没停留两秒钟——这两秒钟是根据这个世界的钟计算出来的,不过我估计他的表在路上早已四分五裂了,他就大为评价说无论是亿万兆公里地,还是亿万兆的亿万兆公里地都可以走完!总而言之,他唱了很多称赞救世主的颂歌,听起来有些肉麻,以致于那边有几个高尚思想的人开始并不愿与他握手道好,这个人一下子变为保守派,快的令人费解!被称为俄罗斯风度。我再强调一遍:这只是传说。我卖的东西是根据批来的,怎样批怎样卖。在我们那里关于这类事情至今还流行着这样的观点。”
“总算让我抓住你了!”伊万几乎像小孩子那样兴奋地大叫起来,可能总算记起些什么了,“那个亿万兆年的小笑话是我自己编的!编故事的时候我仅仅十七岁,还在念中学……当时编好了之后就讲给我的同学听,他姓柯罗夫金,这是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这则笑话的特点非常鲜明,我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听来。我原本已忘了它……可现在我无意之中突然想到了——是我自己想起来的,并不是你告诉我的!很多事情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想起来,有可能在赴刑场的那一刻……同样,这则笑话也一样,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想起来的。你就是这个梦!对了,你是不存在的,你只是个梦!”
“按照你妄图否定我的坚定决心,”客人笑着说,“我认为你是信任我的。”
“从来没有过!连百分之零点一的信任都不存在!”
“可是千分之零点一的信任还是有的。顺势疗法的剂量也许是效力最强的。但承认吧,哪怕只有万分之零点一……”
“一秒钟也不信!”伊万万分愤怒,“可我却不情愿相信你的存在!”他突然很怪地补上一句。
“啊哈!总算承认了!但我心很善良,在这方面我也要帮你一把。记住了,不是你抓住了我,而是我抓住了你!我特地把你已经忘掉的笑话说给你听,目的是让你永远相信我是不存在的。”
“说谎!你到这儿的原因,恐怕就是要我相信你的存在。”
“对。可是,动摇、惶恐,信与不信的感情斗争——这一切有时对你这样识羞耻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惨了,真的不想活了。正因为我了解你潜意识里还有一些信任我,相信我的存在,才说了这个笑话给你听,这样总算最终把不信任的药片放进你的大脑中。我几次让你走在信与不信的边缘,这里头我自然有自己的原因。这是一种新方法:当你根本对我的存在不屑一顾的时候,你马上对我表示,我不是梦,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物,我已经摸透了你的一切;那时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而我的目的正大光明。我只要往你身上撒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名字叫作信仰,就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你坐在这棵大树上将情愿成为在寺院苦苦修行的高僧和冰清玉洁的仙女,因为你心底十分想向这方面发展,你会用昆虫当食物,到荒山野岭去挽救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
“那么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是在拼命挽救我的生命喽?”
“至少应该在某一个时刻做些好事。你不高兴了,只要我盯住你,你立马就生气!”
“滑稽的小丑!你难道在某个时刻勾引过那些把昆虫当食品、露宿荒野,祈祷平安十七年,浑身长出苔藓的仙人吗?”
“各位朋友们,我正是干这个工作的。有时候整个地球以及外星球都能够忘却,我都要紧紧套住这一位仙人,因为他的身价很高,要知道钻石和他的身价是相同的,这样一颗心有时能换回一个星球——我们是按自己的计算方式来算的,这是多么令人珍惜的胜利啊?事实上,这些人中有一些人的素质很高,甚至超过了你,但你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明白信与不信这两个蕴含深刻道理的词句,有时让人觉得只差那么一哆嗦——一个人就会像演员戈尔布诺夫所说的那样‘一个倒栽葱’摔下去。”
“如何,有没有被人耍了,甚至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亲爱的老友,”绅士意味隽永的讲道,“不要介意被人牵着鼻子耍,这总比把鼻子也丢了的好,这是前几日一位有侯爵头衔的病、年轻人(可能是专家为他治病的)向神父耶稣忏悔时所说的话。当时的我真是看呆了,在场的人认为妙不可言。”
“把我鼻子还给我!”那位侯爵说着,猛捶自己的胸膛。
“我的孩子!”神父搪塞,“各种事情都按照天主不可测知的意思一一实现,有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但非同寻常的好处会因为一桩显而易见的不幸而带来。如果你被严酷的命运割掉了鼻子,请不要难过,其中的好处在于您这一生再也不会有人敢对您这么说:您碰了一鼻子灰。”
“神父,这话并不能给我安慰!”倒霉的侯爵十分难过的乞求,“相反的是,我高兴每天碰一鼻子灰,只要它能呆在我脸上原来的地方!
“我的孩儿!”神父叹息着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可能呢?二者不可兼得,如果这样你难道不是在责怪上帝吗?事实上上帝因为这件事还惦记着你,既然您刚才大声叫嚷愿一辈子碰一鼻子灰,我可以间接地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因您失去了鼻子这件事本身,不正说明您已经碰了一鼻子灰吗?”
“真是个大笨蛋!”伊万大声说。
“亲爱的朋友,我只为了引你笑而已,但我要真的发誓,这的确是耶稣会诡辩术,我还要发誓,我说的事情与事实完全相符。这件事情拖了很长时间,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那位倒霉的青年人回了家,那天深夜便开枪自杀了。直到那一刻我才离开了他……。至于那些耶稣会士的忏悔室,真正是我消愁解闷的绝妙去处。我再告诉你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一个二十几岁的金发女郎诺曼底来找老神父。女郎长的十分水灵、丰满,是名副其实的天生丽质——让人不肯让目光从她身上离开。她弯下身子,向神父轻轻诉说自己的罪过。
“我的宝贝,你不会又陷进去了吧?”神父神色诧异,“啊,Sancte Maria,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已不再是那个男人了,但若是这样子,何时是个尽头,您怎么不害臊呢?!”
“Ah,mon pire,”姑娘带着沉重的负罪感哭着回答,一脸诚心悔过的样子,“Ca lui fait tant de plaisir,et a moi si peu de peine!”
“有谁能够想到,她的回答竟然是这样的!听到这里,连我自己都颤抖了一下:这是自然本性的呼唤,在我看来,这比守身如玉更好!我立刻免了她的罪,转身要走,但立刻又回来了,我听见那个神父在小洞里正在约她晚上幽会。这老东西看上去十分正经,刚刚才几秘钟的时间便陷了这么深!这是人的真实性格,本性总是要十分突出的表现自己!怎么,又扭头不睬我啦?又不高兴了吗?我可真没办法讨你的欢喜了……”
“我只重复一遍,你不能对我约束过紧,别要求我‘尽善尽美’,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会很友好地相处,”客人十分随和地说着,“我不在红光中出现,陪伴着雷电交加、张开焦黑的翅膀出现在你的身边,你生我的气真正原因在于我的这副穷酸样。在美的体验和自尊心这两点上你都受到了打击;来认识一位有头脑人物的恶魔为何竟是如此平凡的东西?总之,你身上那种早就被别林斯基狠狠地挖苦过的浪漫气质还是存在的,是年轻人嘛,有什么办法呢。刚才在见到你之前,我在思索一个问题,想跟你开个玩笑,把自己装成一位退职的四级参议官的样子,曾工作于高加索,有一极显眼的狮日星勋章挂在燕尾服上,但是到底不敢造次,因为我在燕尾服前襟挂的只是一枚狮日星勋章(你认为至少该挂北极星或天狼星勋章),我担心,光就这一点你就会把我打一顿。你天天骂我笨蛋。但是,我的上帝,我并不想和你较智力,靡非斯特我见浮士德的时候自我了解说,他想作恶,可是到处做好事,他喜欢怎么说就由着他说,我却恰恰不同,众多人物中热爱真理和与人随和相处的,除我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人了。当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子’怀揣被钉死的悔悟的一个强盗的灵魂升天时,我在场听到了很多小天使们高唱赞歌。高扬的声音已经快要从我的胸口迸出来……你也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容易动感情,艺术细胞特别丰富。但理智——啊,这是我性格中最倒霉的地方——理智在这里也不让我的举动出格,我舍掉了一刹那的冲动!那时我在心里念着:如果我唱出了赞美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世上顿时将没有了颜色,不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完全因为我的个人地位以及忠于职守的责任心,我必须把这样美丽的动机扼杀在自己的摇篮中,接着干我自己的卑鄙的事情,做好事的光荣全给了别人,剩下的都是干的坏事情。可我一点儿也不希罕骗来的各种荣誉,我不爱出风头。可怜的我为何总要遭到所有正直人的咒骂,我甚至经常忍受别人的拳打脚踢(化成人形有时候就得准备承担这样的后果)?我明白这其中的关键所在,但别人怎么样都不愿告诉我实情,原因是如果我知道这个秘密,或许会大声地唱着赞美之歌,到那个时候不可或缺的负数就会消失无影,以后世界平安,但那并不是好事,说不定正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末日,以至于报刊及杂志都无人问律,因为到那时谁还要去订阅?我明白自己到最后只能听天由命,我必然会走完我的亿万兆公里地,然后了解秘密。可是在这一天还没到来的时候,我必须硬着头皮:认认真真地完成我的使命,毁掉千千万万个人,使一人得救。打个比方,为树起一个正义的约伯的形象,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玷污了多少人的清白,破坏了多少人的名声,为了他,还恶毒地把我当猴耍!哼,在揭开谜底之前,对我来说,有两种真理:一种是我的,一种是他们的。现在还不明白哪一种更准确……。你不会睡着了吧?”
“当然喽!给你说的不睡着才奇怪呢,”伊万恼怒地嚷道,“这些都是我骨子中愚笨的部分,而且是我早已准备把它克服、淘汰了的,我自己把它们弃之如死尸——没想到却被你拿来当作什么有趣的东西来端给我!”
“真惨,我一番好心你又不接受!我原本还准备用一种文学的铺垫方法慢慢地取得你的信任,说真的,那个星球呈给我高唱赞歌的效果不错吧?接着是刚才那种模仿海涅的讽刺口吻,不是惟妙惟肖吗?”
“唉,我从来不是这样一名奴才!为何我的魂魄会出现类似你的奴才?”
“亲爱的伙伴,我知道一个对人十分喜欢和非常可爱的俄国青年,是个青年思想家,热爱文艺,他自编的一本史诗十分好看,题目是《宗教大法官》……我总是惦记着他!”
“我讨厌你又说那个《宗教大法官》。”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大声叫着,自己却已羞的无地自容起来。
“那么《地质学上的激变》怎么样?还有没有印象?那确实是一首小史诗!”
“不许再说话,小心我杀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