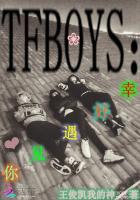九夷王姜懿原本就是个极为敬重江湖豪杰的爽快人,如今接连认识了樊於期、天乾、荆轲等中原人士,自然也是快意无比。待那天乾和荆轲领了司马空入得九夷城之时,姜懿便将早就准备好的酒食饭浆给呈列了开来,以供诸军享用。不过九夷族终究还是戎人的习俗,呈列酒食并不像中原一样用坛、罐、鼎、樽一类的器具,多半是用刚竹穿过牛羊的肚肠,架于木架上用火烤后食用。如若要说饭食用的器具,那便是这竹筒和树枝外加一柄锋利的匕首了。至于清酒一类的饮用食物,则多用牛、羊的颅骨作为盛用的器皿,虽然看起来较为野蛮,不过吃起来倒也显得畅快豪气,樊於期、天乾等人原本也都是豪爽人,所以到了这里就一并入乡随俗,沿用了九夷戎人的风俗庆贺。唯有司马空是杂家文士出生,自然对这种粗野豪迈的就食方式有些不适应,不过既然为客,也不好多说,只好随着众人一起吃将起来。
“哈哈哈,今日群雄毕至,本王能够一下子亲自会逢这许多中原豪杰,也算得上是有幸至极,来来来,本王先敬诸位一杯,粗野之地的粗糙饭食,还望诸位不要介意。”姜懿占地为王,作为主家,自然占了上座,如今对着众人的相聚也是一番豪语,边说着边就要举杯相邀。
樊於期等上庸士卒本已是到了穷途末路的绝境,适逢姜懿收留能够暂居此地,已是感恩在怀,如今受了姜懿这番大礼,如何不惊?连忙也一并起身举杯,躬身还了礼。唯有司马空倒是就座原地并未起身,因为他作为杂家大文士,向来只叩拜君王始祖,要他对这毫无中原文明的蛮荒之族躬身行礼,自然很不习惯。
此时身在侧座的荆轲倒是注意到了这一细节,于是趁着众人起身行酒之际,便朝司马空弯身一躬,盛情而道:“荆某素闻司马先生博学天下,早有仰慕之意,如今能得一见,心中激动万分,薄酒一杯,还望先生笑纳。”
司马空虽说是个极为清高的文人,不过对于荆轲这番主动上前的邀请,也不好拒绝,便举杯还迎道:“呵呵,司马空即便再博学,如今还不是乖乖地落在了小兄弟的手中,墨家钜子,果然非同凡响。”
荆轲听他这番言语,知他心中还对自己用离间之计逼他归降樊於期一事耿耿于怀,于是便十分惭愧道:“在下出此下策,实乃情非得已,还望先生见谅。”
司马空只是莞尔一笑道:“钜子少侠过谦了,当年百家争鸣之时,孔、孟、墨三家独占三甲之列,我杂家祖师一直对此不甚心服,如今我司马空再次输给墨翟的后人,自然也是心服口服了。”
司马空口中的祖师自然指的是吕不韦,如果按照学派来说,孔、孟、墨远要比杂家的创派时间要早的多,然而吕不韦自创杂家学派,又自诩为秦国宰相,门客遍布天下,所以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学派与孔孟等人并列,然而却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特别是吕不韦死后,其所创的杂家学派更是四分五裂,名存实亡了。司马空作为吕不韦的嫡传门生,由于受到了吕不韦思想的渲染,所以也一直自诩清高,不把别家放在眼里。他原本是想在秦国出仕为官,通过建立功勋来达到名扬杂家的目的,可不想如今事与愿违,这功勋非但没有建成,反而倒成了别人的手下败将了,所以他这莞尔一笑,多少带了点苦涩和无奈。
“百家争鸣,原本是中兴天下的大事,又何须分高低贵贱呢?”此时的天乾在一旁也是看明白了司马空内心的苦涩,于是便也端起牛角杯朝司马空举杯道,“司马先生欲成名天下,便如同千里马欲寻得伯乐一般,不在一时之得失。”
“哈哈哈,正是正是,天乾公子金玉之言,本王受益不浅。”天乾这一席话,原本言语之中有褒扬司马空千里马之意,不想话音刚落,却听得一旁的姜懿哈哈大笑之声而来,随口连连夸赞起天乾来。
这姜懿自天乾协助樊於期大破狐竹城之后,本就对于天乾十分器重,之前他还对司马空傲慢无礼的态度感到愠怒,如今既有天乾从中和谐,他不但将之前的愠怒全消,反而心中大悦起来。
“天乾一介江湖游士,并非什么大富大贵的王家贵胄,自然没有什么金玉之言,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天乾直望着司马空,随便用谦逊的言语回了姜懿。
“诶,天乾公子满身才华横溢,有勇有谋,怎是一介莽流所能比?若是肯纡尊居于本王麾下,本王将女儿许配给你,让公子做个乘龙快婿,成为我九夷的太子,那岂不就有了金玉之言了?”那姜懿说道兴头上,竟不顾自己女儿在场,便当着众人面说了这番话来,直把一旁坐下的公主姜萼羞得满脸通红。
那姜萼原本是戎人出生,性子本就顽劣粗野,从不轻易红脸,不想今日竟被父亲此言说的面红耳赤,顿时十分尴尬地叫嚷起来:“爹爹,你尽瞎说!我不理你了!”嚷罢,便独自一人遮掩着脸面跑了出去。
“萼儿,萼儿!”尽管姜懿连着喊了她几声,却仍然无济于事,那姜萼只顾着跑出殿外,根本不理会父亲的呼喊。
待那姜萼出了殿门,消失在众人视线外之后,姜懿这才无奈地轻叹了一声,既是爱怜至极,又是无可奈何,随后又向众人致歉道:“小女自小被本王惯坏了的,所以性子有些不恭,还望诸位不要见外。”
众位知道这女儿家的事本就让人捉摸不透,这九夷王又不分场合的这般说道,姜萼有此反应也是情理中之事,于是也纷纷向九夷王抱拳谢礼,以示会意。天乾在还礼之时,更是不忘朝姜懿阐明道:“公主终身大事,还是让她自己做主为好,以后这样的戏言,还请九夷王不要再向天乾提起了。”
这姜懿哪里是一句戏言,分明是有心要向天乾提及,他赏识这位年轻人已经许久,如今趁着这机会故意提及,本来是想让在座的诸位做个见证,可不想如今却被天乾轻描淡写地回绝,顿时觉得心中一番话堵得厉害,却无从说起的感觉。他正想理了头绪向天乾解释一番,可熟料刚刚张口,便听得座下戍卫回报:“启禀大王:离城十里之外发现中原军队的踪迹,据了望台的守卒估约,其部众不下十万余人。”
“十万之众?!”姜懿方才还准备为自己提及嫁娶一事解释一番,忽然听得戍卫有此奏报,顿时惊得双目瞪视,脱口而出。
“其前锋的旌旗之上可是黑色帷幕作底,金黄花纹绣边?”此时身在右座之下的司马空正襟危坐,表情淡然,十分镇定地向戍卫问话道。
“正是。”戍卫点头应道。
“那便是了,潘党的动作倒是挺快,看来秦军要深入九夷了。”司马空听了戍卫的回话,随即便自言自语道。
众人见他如此自答,都不免面面相觑,不知那司马空怎么这么快就推断出是潘党、桓齮的军队。只有天乾和荆轲听出了其中的门道,无不对司马空招招见血的问话叹服。
“司马先生何以知道这部众便是秦军的部队?”姜懿听了司马空的言语,倒是一头雾水,十分不解道。
“先生对戍卫不问‘秦’、‘桓’等字样,因为他知道这些戎人未必会认识中原人的文字,到时候结果反倒是容易含糊不清,他只以秦国旌旗的颜色构造相问,如此通过戍卫的回答便可轻而易举推断是桓齮等人的部众。”此时的天乾扬起手中的羽扇,望着司马空慢条斯理地解释道。
“哦,原来如此。”姜懿身为戎人,自然不懂的秦国旌旗的搭配构造,如今听得了天乾的这番解释,顿时恍然大悟,心中也是大为赞赏,不过他这份赞赏之意不是对于司马空,反倒是对解释了此事的天乾赞赏。
“哼,来的正好,樊某正想好好会一会这桓大元帅!”此时座下的樊於期听得司马空所料来者乃是桓齮的部众,心中积聚了多日的恶气顿时涌了上来,啪的一声放下手中的羊角杯,赫然厉声道。
“樊将军请放心,你等既来我九夷之地,那便是我姜懿的贵客,你若决心要与秦军一战,我自当全力助你!”姜懿见樊於期面露愠色,知道他痛恨秦军久矣,于是便也跟着一起发话助威道。
“倒不知樊将军与九夷王手下有多少部众?”这两位首领一股子愤慨的言语刚落,哪知端坐一旁的司马空忽然定声而问道。
樊於期循声看了司马空一眼,却见他面色从容,从容的竟有些不顾自己的这份怒意,于是也就随口一回道:“樊某有上庸精兵上万之众!”之前樊於期与杨端和在上庸举事,因贸然深入九夷之地,已经折损不少,如今且剩余上万人,其中不过也是老弱病残占了不少。樊於期这般答话,实则不想输了自己的威风与士气。
“本王九夷城中也有戎族部众上万,如若再发信联络九夷的其他各部,三日之内定也能集合个五万之众。”姜懿不明白司马空此问何意,只是据实作答。
“樊将军虽称有上万之众,充其量也就一万人马,还不算那些老弱病残之卒;九夷王虽也有上万之众,依然不过一万人马,而秦军已经迫在眉睫,根本不会让你有三日的期限去筹集人马,所以目前加起来也就两万人。而据我所知,仅桓齮本部便有十万人马,还不算潘党等偏军的部众,如此一来,两军的实力悬殊已经立现,樊将军难道要作以卵击石之举吗?”司马空听了樊於期和姜懿的答话,便又不紧不慢言语轻淡地分析了一通。
“哼,我上庸军个个是训练有素的将士,又何惧他桓齮的不义之师?”樊於期显然对于司马空的这番理智的分析颇为不服,随口便又反击道。
“上庸军骁勇善战众所周知,不过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自杨端和率领上庸军卸甲归田之后,如今已经时隔这么久,樊将军难道还能保证眼下的军队有当年的勇猛善战?倒是桓齮所率的秦军乃是蓝田大营本部精兵,日夜操练多年,已经是身经百战,这才会破起韩、赵来如此迅速。再退一步讲,就算上庸军依然是骁勇善战,再加上九夷天险的相助,此番想要以少胜多,也是未知之数。即便胜了,那也是惨胜,如若秦兵再举兵前来,那樊将军又拿什么与之相抗?”司马空依旧是轻描淡写的言语,却叫人不得不折服他的言辞。
“司马先生,我等是仰慕先生的才华,这才千方百计邀先生一聚,如今先生何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司马空的话虽句句在理,却叫樊於期听得心中极为不快。
而此时座下的荆轲则已经听出了他二人言语之间的矛盾来,于是嘿嘿一笑,分别朝樊於期和桓齮道:“樊大将军的神勇是天下皆知,区区桓齮自然不在话下,不过司马先生既有此问,想必亦有巧夺天工的妙计在胸,不知先生肯否向众人示下?”
“哦?难不成这位先生果真有以少胜多的妙计?”姜懿听得荆轲这般言语,便也一下来了兴致,朝那司马空发话问道。
“妙计不敢当,区区雕虫小技倒是有一策,但不知樊将军可看得上否?”司马空虽是在答姜懿的问话,但目标直指樊於期,却是要看樊於期如何作答。
“樊某一介莽夫,愿闻司马先生妙计。”樊於期虽说心中对司马空有些不服,不过碍于大局,自然也不好拆他的台,便双手一拱邀他说道。
“樊大将军在秦国为将多年,想必已经对秦军的士风了如指掌,司马空方才观将军之风范,倒是与桓齮颇有些相似…”
“哼,那桓齮奸贼怎能与樊某相匹,司马先生这是要故意羞辱樊某吗?!”司马空刚刚把话说了一半,樊於期便就一声低沉的怒意将他的话打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