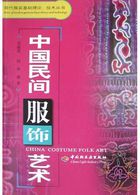捕头胡茂大摇大摆地行在沿河的平坡路上,他遥遥可见一长排低矮的塌房,还有泊岸交易的商船,也有忙碌的壮工和看守塌房的白役。他行至码头处,无意间瞥见了人群中的周中天,他冷冷笑出了声,唾骂道:“呸,不识时务的废物,你也就这个狗命了。”
码头处人来车往,尤其喧闹嘈杂,虽然土地湿软倒也平坦可行。一个眼尖的牙人看见了胡茂,他匆匆跑来身旁点头哈腰:“胡爷,您来了!上月的钱恰好结算完毕,正等着您来点收呢!”
胡茂手按刀柄,转脸看着他点头说道:“嗯,待会走时给我,不过从今往后,你们都需收敛些,钱还是照收不误,但是你们的手脚得干净些,莫要留下什么话柄,懂吗?”
牙人诧异地问道:“胡爷,这到底怎么回事?”
胡茂看了眼左右,拉着他往人少的地方走了几步,压低声音说道:“新任知县的手段厉害得紧,在咱们还没摸清他的性格之前,谁都要老实点,你们最好别给我添乱。”
牙人昂首挺胸,不以为意:“不就是江解元嘛!听说他错过了考期,朝廷特许他先任知县,三年后再临考场,他一个二十岁的小子,还能翻了天不成?能唬得住谁呀!”
“不管他有没本事,好歹也是一任知县老爷,起码捏死咱们是绰绰有余的,谁会傻到往枪口上撞?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尽量老实点。”
“明白,我会去转告其他弟兄的。”
周中天扛着一袋货物,他远远看见了胡茂和牙人,他知道当晚带头打他的正是胡茂,他目中的怒火忽闪忽逝,他咬了咬牙,继续做工。胡茂似是察觉到不善的目光,他转头去看,恰好看见周中天转身的背影,他眯了眯眼睛,对牙人吩咐道:“他叫周中天,你记住他,以后每逢双日子,你减他一半的工钱,每逢单日子,让他白天滚蛋,只准他夜间做工。”
牙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周中天,狞笑说道:“胡爷只管放心,一定照办。”
胡茂志满意得地点了点头,问道:“最近妓馆里有没什么新鲜货色?”
牙人嘿嘿笑道:“正好,昨夜一艘商船送来一个,不过只有十五六岁,大概也叫人破了身子。”
胡茂摆了摆手:“无所谓,解解闷,泻泻火而已,带路。”
“胡爷,您请。”牙人先行一步。
此处的妓馆全由私人经营,妓馆一般建在临近塌房的地方,往往妓馆的娼妓都是来路不正,大抵是遭人欺骗拐卖或是强行掳来的,所以姿色相较秦淮河要逊色许多,不过毕竟只供壮工发泄,也无人会去挑剔。
牙人抢先一步掀开了妓馆的门帘子,然后立在一侧尊请胡茂先进。妓馆里闲坐的主事一见胡茂进来,真如见到了天王老子,连忙起身凑上去阿谀奉承:“胡爷,您可是难得光临一次,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胡茂趾高气扬地侧过身去,带笑骂道:“你胡爷可是衙门里的公差,哪有时间整天往你这破地方钻?听说你这儿来了个新货,所以想来试试,如果新货还不错,算你走运,这往后你胡爷我便是你哥,你有事没事吼一嗓子,爷自会帮你摆平。”
“啧啧…能得胡爷如此关照,小的真是受宠若惊,深感大恩,深感大恩…”主事哈腰作揖,脸上笑开了花,他直起腰来指向一边上锁的屋门:“这新货就在此间,请胡爷慢慢玩耍,小的们在外候着。”
他过去开了锁,便与牙人一起走出了妓馆。胡茂按着腰间佩刀,喜笑颜开地进了屋,这是一间窄小简陋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歪斜的破床,床上的被褥也已开缝。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蜷坐在床头,她秀发散披,环抱双肩,她一见胡茂进屋,不禁瑟瑟发抖,像只小麻雀惊恐地盯着胡茂,眼中亦有泪花闪烁。
“小妹妹,莫怕,爷可不是坏人,爷是专门来疼爱你的。”胡茂一脸阴沉的奸笑,他探手慢慢靠近床头,突然展开双臂宛若鹰隼猎兔,纵身猛扑上去,一把按住了小姑娘,然后使劲将她翻倒在床上。
“你走开,你走开…”小姑娘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双拳不住地捶打胡茂。
胡茂一双不老实地粗手,早就开始揉摸、拉扯。此时见这小姑娘竟敢反抗,胡茂恼火地给了她一巴掌,随后又是反手一巴掌,瞪眼吼道:“你这是想死么?爷可没什么耐心。”
这小姑娘已被打得头晕目眩、唇口绽裂、鲜血横流。胡茂见她终于老实了些,当即扯破了她外裳,然后像头蛮牛似的埋头拱了下去,接着便解带褪裤。小姑娘反抗不能,默然淌泪,又不堪羞辱,不敌身心俱痛,只得愤然咬舌。胡茂正在行事当中,此时才发觉身下人不吭不响,他并起双指搭在小姑娘的脖颈处,竟已没了跳动。
胡茂破口大骂:“他娘的,你要死还不能等爷先完事?”
他骂归骂,但是动作并未停歇,他依然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地折腾了半个时辰,直到身下人身子骨凉透,他才肯罢手起身。妓馆外边的主事和牙人,没能听见屋里的动静,他们相视一眼,然后一起走进了屋,只见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姑娘,躺在破陋的被褥上一动不动,嘴角还淌着鲜血,鲜血沿着脸颊流了一滩。
妓馆主事吓得往后倒了倒,他扶住了身后的土墙,惊恐地看着一旁穿衣系带的胡茂:“胡爷,这…这是?”
胡茂穿戴好衣帽,扣上佩刀,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自杀了,你们找个地儿给埋了。”
主事和牙人脸色惨白,他们抹了把额角的冷汗,只能按照胡茂的意思去办。于是他们两个便用被褥裹住了小姑娘,但是这青天白日的,当然不可抬出去,如此两人稍一商量,还是决定等到深夜时候,再偷偷运往河边埋葬。
自从赵主簿和刘县丞离开之后,至此还没见一个人回来禀报详情,江城子坐立不安,便在花厅内来回踱步。他刚去牢房里看望过江城锦,虽已经过了救治,可是重伤未醒,他临走时便吩咐狱卒要特别关照。
江城梦此时火急火燎赶来了衙门,差役自然认得他,将他带到了花厅。他刚迈进花厅,焦虑地说道:“江城锦到底怎么回事?族里的长辈遣我过来问问。”
江城子当下便将讼书的内容讲了一遍,也说出了自己的猜想:“我怀疑是张德亮设局陷害的,如今江城锦重伤未醒,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出门走访的捕快和百合也没回来,我正在等待他们的消息。”
江城梦一听此案兴许是张德亮陷害的,他坐去一旁的圈椅上,摇了摇头说道:“若真如此,此事必然棘手难办。”
他抬起头来,严肃地说道:“你记住,千万不可徇私舞弊,如果江城锦真的犯了事,你也不能手软,这关乎到你自己的安危,张德亮此人心胸狭隘,他一旦发起疯来,肯定会死死咬住人,假如真闹到了应天府,我们不一定讨得来好处,族里的长辈没来烦扰你,便是不想给你增添负担,他们的意思也是希望你能秉公办理。”
江城子点头说道:“大哥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江城梦起身走来面前,说道:“我想张德亮如果知道我们江家族里没动,他也不敢随便惊动应天府,毕竟我们两家一旦较起劲来,定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局面,所以,你有充足的时间调查此案,假如此案与江城锦无关,张德亮又落定念头想整死江城锦,我们江家族里绝不会袖手旁观。”
他拍了拍江城子的肩头,转身离去。
他前脚刚走,衙门的差役后脚赶来花厅:“大人,衙门口来了一群姑娘,她们说要见江城锦,如果不许她们见,她们便要硬闯衙门,还要去牢房劫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