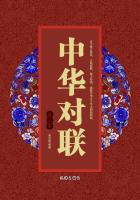于贵锋
无事读唐诗。翻到王维部分,有一首《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突然就想起古马的一首《归来》:
两手空空我从外面回来了
牵牛花和青藤的柴门
是我站在露水中的哑妻
我空空的两手一点灰尘都不带
展开双臂便能拥有今夜的你们
妻儿呀
两首对读,仿佛是一千多年后,古马对王维的回答。
晚年王维居住的蓝田,李商隐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句,足见此地之美,也可从王维自己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得到印证。作为送别诗,王维对“守妇思念离人”的这个传统题材进行了巧妙的转化,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通过对“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巧妙化用,将一种已知的结果(不归)依靠时间的暗示(日暮、明年)和疑问置于一种不可知当中。既存在着希望,又使那希望处于怀疑,形成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情感状态。这是真正的煎熬和折磨。此后许多诗人,都对此做了痛苦的注脚,什么“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等。但无论怎样,都更多地倾向于“归和不归”的“不归”,并将此作为一个预设的背景。
当然,王维的发问仿佛脱口而出,又仿佛内心的自问。如果离开是必须的,则随着日暮将柴门掩上,必将自己也“关”了进去,只剩下对结局、未来的猜测和怀疑,空气中只剩下那一声发问,等待着被“行人”听到并作出回答。
这当然具有人生和哲学的意味。
古马就像行人,仿佛在一千多年后,他机缘凑巧,或者说心有灵犀,终于听到了王维的那声发问,“归来”了。
仍旧是“牵牛花和青藤的柴门”,仍旧是“露水”,仍旧是人与自然相处与共的、令人熟悉的场景:我回来了,但“两手空空”;那等着我的人仍旧“站在露水中”,但她已经变成哑巴(“哑妻”)。
这种令人心惊的悲凉岂能用言语形容?岂是个人一己的悲哀?“站在露水中的哑妻”,这是一尊穿越了时间、仍在哭泣和盼望的雕塑。
如果古马的“回答”到此为止,也只能是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将场景彻底还原到“守妇和离人”这个基本情感模式内,并将关注的重点也落脚到守妇的“苦”与“等”上,但根本上仍旧是历代中国诗人无法摆脱的抒情点,唯一的不同就是通过“离人”的一无所获反衬“守妇”的痛苦,加重这种空守的悲哀感。
心灵的交流开始于接下来的一行:
我空空的两手一点灰尘都不带
这在表面上对“空空的两手”的强调,在结构上和开头形成对应的同时,却开启了新的语意。“灰尘”,那是追寻的结果,也是追寻在心灵上所落下的疲惫,隐含着行人无数的挫折、沮丧和失望,也使归来的行为成为一种怀着疑虑的必然。当看到“守妇”仍在等,归来成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心,也开始尝试着“归来”,“一点灰尘都不带”。这是一种自觉的心灵擦拭行为,是一种宗教式的忏悔。又由于“灰尘”出现在“露水”后面,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来回味“露水”的寓意,——至少那种擦拭,是行人蘸着“露水”,行人和守妇之间由于离开、时间等割断的联系在这种擦拭中重新建立了,从“外面”到“柴门”这样外在的联系,也实质上是情感上的联系。
至此,“我”才能够“展开双臂”,也才能“拥有”,也才能有更大的惊喜(哑妻到妻儿的变化),才能够真正归来。
古马也就此将一个简单的“守妇离人”故事,演变成了一个隐含着更大、更广泛人生意义的象征。
这不是简单地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如同王维对楚辞中那句诗的化用和改变经历了一千余年,古马对王维的回答又经历了一千多年,而在这中间,人们在追寻和等待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忽略。就像归来的尤利西斯,我们希望他能够在爱情中安睡,就像人类在时间的臂弯里。但“灰尘”既然要用露水擦拭,难道我们就因此能否认它存在过或者说就能肯定它已经不存在了吗?像看到站在柴门前的哑妻我们就能否认柴门里还藏着一个孩子吗?
但人类的某些精神,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得以延续和贯通,如同春草、牵牛花、青藤的不断更替中一个孩子却在旁边悄悄成长。诗人们也跨越时间的阻隔,将归与不归、留守与离开、发问和回答等置于一个更大的“场”,令人顿悟“诗歌原本就是心灵的在场”,并且因此牵出了一个诗歌母题清晰的线索:无疑,归来之路是漫长的。
原载《九龙诗刊》2007年春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