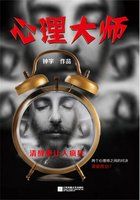事情已经办结完毕,没有引起多大动荡,基本达到了乡里、村里和群众满意。就在临走的时候,同志们说,杜局长难得回老家一趟,我们先走,你留下来,再与家人团聚一下。杜思宝想想机关里近来没有什么大事要处理,就给范哲母女打了电话,说在老家住几天,一个人留了下来。
杜思宝是个孝子,在家的几天里,主要是守在母亲身旁,与母亲一起,回顾了不少陈年往事。
母亲对他说,心肠好、勤劳的贵亭叔,还有一生只有一技之长的栾二哥,已经离开了人世。老支书刘庆典偏瘫了,经过抢救,总算是保住了命,现在说话呜呜啦啦的,一点也找不到过去威风八面的影子。狼叔的满嘴牙掉光了,他儿子刘继华给他安上一嘴瓷牙,吃罢饭,就得摘下来,泡在清水中。这老家伙,这么多年来,再也不当三只手偷东西、不“咬槽”了。嘴赖的发旺哥两口子,果然留在了南方,肯定不会回来再与土坷垃打交道了。孙乃社依然健在,还住在戏楼里,不写诗了,也不写对联了,逢人还要卖弄自己读过的《封神演义》。祖师顶上的“静宇”道人有时下山来,或者参加县政协会议回来,总要拐到他那里坐坐,画了一些符咒,以及带来一些杂七杂八的算命书籍,让孙乃社老人兜售,也能换一些钱,也不知两个人是否分成。别看高恩典的孩子那么多,可这个人很有办法养活他们。大一点的出去打工,小一点的在家上学。穷日子过惯了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知道俭省,他的孩子在外边省吃俭用,给家里寄的钱最多。现在他们一家搬到了高楼街,盖了门面房,专门做收购破烂的门头生意。有钱了,人就活得得意,当年的那个女副乡长,现在到城里一个部门工作,真的把他那个长得最漂亮的小女儿认下,做了干女儿,两家不断有来往。
母亲告诉他,你那个在湖北当农业工人的凤桐叔一家,已经联系上了。你叔不在了,现在变成了三家,你婶子跟他们的二儿子过。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彻底成了湖北人,多数还对老家有感情,个别的就不好说,咱们马寨在他们心目中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你要是有空了,去看看他们,不要割断了联系。杜思宝一边答应,一边在心里说,应该去看看,不要说是血脉所系,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说不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也在那里可以找到。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请他去吃了一顿饭。叔叔腰里别了个手机,叫杜思宝感到惊奇。他婶说,前几年,谁要是有了手机,大家都感到惊奇,现在谁要是没有手机,大家反而感到惊奇了。这手机的用处大着呢,在地里干活,可以同小磊他们联系。谁家死了人,也可以打手机,让你叔给他们准备棺材。你到门口看看,你叔的手机号码在门上头写着呢。杜思宝来时并没有注意,出去看看,果然在门楼下边,赫然写着:订购棺材热线电话:135××××××××。心里好笑,现在叔叔也重视广告效应了。他想起,前几年,有一则短信说,乡下人抱怨城里人,“我们刚吃饱饭,你们就闹减肥了;我们刚吃上糖,你们得糖尿病了;我们刚用纸擦屁股,你们却用来擦嘴了;我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就包二奶了”。看看叔叔家里的种种电器,一应俱全,不禁想到,城乡差别也许有一天会消失的。这世道沧海桑田,变化真快、真大。
当年那个跑来的婶婶告诉杜思宝,自从小磊把许翠翠拐跑以后,刘臭蛋的母亲每天指桑骂槐地羞辱他们。谁知道刘继宗的病竟然因此好了,他妈说,原来继宗的病,都是许翠翠这个骚婆娘“妨”的,气自然消了。后来,刘继宗有了杜思磊给的那笔离婚款后,又娶了一个媳妇,日子过得虽然紧巴,好像比以前还强一些。杜思宝听了很高兴,因为他在老同学刘臭蛋面前,从来不敢提这件事儿,好像替小磊有愧,觉得对不起人家,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叔叔的院子里,电动的木工器械更新了不少,就差用电脑进行数控了。另外停放着四轮拖拉机、耘播耧等农机具,拖拉机的拖斗还是液压升降自卸的。叔叔对他说,现在种地真省劲儿,没有人肯出笨力了。寨子里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国家把提留统筹农业税免了以后,上级还发各种补贴,在外打工的回来了一些人,结果没有心在地里干下去,过不了多久,又各奔东西。寨子里的有钱人都到县城、高楼街上买房子,做买卖。听说南河和北河的下游,国家准备修大型水库,当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辅助工程。工程动工前,咱们寨子还要移民,我看咱们马寨没有几年的寿命了。杜思宝说,走着看吧,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搬到唐都市去,我们在一起住。杜凤梧说,那倒没有敢想,再说,你婶我俩到城市去,肯定不习惯。
在叔叔的堂屋西头,杜思宝又惊奇地发现,这间屋子里,保存了不少犁耧锄耙、石磙、石磨等农家用具,都是些许多年不用、见不到了的东西。尤其是那一个浑身全是斜眼儿的耩地用的木耧,还是崭新的。杜思宝问叔叔放这些东西有啥用?快嘴的婶子嘲笑说,你叔叔是个有心人啊,中央台有个“鉴宝”节目,都是一些老古董,你叔叔看了后说,没准哪一天,咱家这些东西也是宝贝。他有空就搜集这些不攥粪东西,准备给孙子留着,让他们有朝一日,到中央台去参加鉴宝节目哩。
在小暖家里,杜思宝见到了才几岁的小侄子。小家伙虎头虎脑,非常可爱,头上留着一个木梳背儿,脑后留着一个鳖尾儿。杜思宝一下子又想起了七太爷,想起了七太爷的那条辫子。这家伙说不定就是当年的七太爷转世,与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差不多。同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背着小暖,在寨子里到处逛的往事。那时候,小暖也是这么大,没有留这些东西。没想到,小暖给自己的孩子这么打扮,让人觉得别扭。
小暖对他说,哥呀,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对学习不感兴趣。你的大侄子,整天瞎胡混,眼看初中毕业了,成绩很差劲儿。回到家里,就知道看电视。近来,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马尾、竹筒儿和花梨木棒,在我的车床上旋来旋去,做了一把弦子。星期天回来,成晌在屋里吱吱扭扭地拉,就好像杀鸡子,难听死了。他妈说他不务正业,他说是学成了,长大后要参加省里的“梨园春”大奖赛哩,把我们两口子气得没有办法。可咱妈护着他,竟然说,学吧,学吧,奶奶爱听你拉弦子。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遇到了荒年,拉上弦子讨饭,还能多要到一些红薯干哩。你听听,这老太太说的是啥话!
杜思宝想,几代人的思维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妈妈能说出现今人想都不去想的话,自然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现在一想起那个挨饿的年月,就可惜在酒桌上的好酒好菜,有多少被白白地糟蹋了。
杜思宝不爱串门子,除了到叔叔家、小暖家吃饭外,只到元叔那里坐了坐。元叔对他十分客气,没有表现出来早年他们之间有多么深厚的情谊。说起他的孩子来,元叔只说,还行,都能够自己挣一碗饭吃。杜思宝想趁元婶不在身边时,问一问他,跟凤姑联系上了没有?终于忍着,没有问出来。
他又抽空在寨子里经常魂牵梦萦的地方看看,寨子里原来所有的景物都悄然发生了变化,变得自己认不出来了。实行了村镇规划后,各家各户的房子盖成了排,有楼房、平房,也有老瓦房,不怎么整齐。有的墙上写的是村规民约,字体倒不错,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更多的是写的大标语,内容都换上了新词,主要是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寨子周围的寨墙没有了,与寨外的房舍连成了一片,整个寨子膨胀了几倍。在当年他们这一茬人,用铁皮筒喊广播的地方,现在夷为平地,种了花草,修了路径,盖起了象征新农村的一个厕所。涂红的砖墙上,竖起的是用天蓝色塑料瓦制成的尖尖屋顶。跟着他的孩子们说,这是乡里安排盖的欧式建筑,没有人肯在里边拉屎撒尿,还不如到野地里撒着痛快。
最让杜思宝感到高兴的是,胡万有打手机说他回到了县里。杜思宝说,我也在老家,让他马上回来见面。又给孙二孬打了电话,孙二孬表示也要回来。此外,仍然当着派出所长的刘继华,听说这几个人都回来了,也赶了回来。这期间,刘继苹正好在家里伺候她父亲,知道杜思宝也在家里,过来坐了一次。杜思宝的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亲热得像对待自己的儿女。刘继苹说,婶子,我做梦经常梦见你呀。
杜思宝没有料到的是,孙丫丫跟着她哥她嫂子,也一同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娃娃。他们去看杜思宝的妈妈时,孙丫丫逗着自己的孩子,说叫奶奶,叫奶奶。杜思宝的妈说,别说他不会叫,就是会叫,也应当叫妗子。马玉花说,你老人家就别论辈了,论年龄,他就应该叫你奶奶!杜思宝妈妈连连点头说,感谢主,感谢主!
刘臭蛋在自己家里办了酒席,请大家到他那里团聚。他们把元叔、刘庆河支书、高恩典也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少有的亲热。
在入席前,刘庆河对大家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元哥的小儿子孙松鹤博士毕业后,现在分配到一个县当副县长了。
大家一听,非常高兴,纷纷向元叔表示祝贺。
杜思宝说:“元叔,大喜呀,现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当一个公务员要凡进必考,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入围。只有硕士生好一些,在市里可以走绿色通道,直接安排。我兄弟是个博士研究生,小小年纪就当上了县长,都是元叔你培养教育的结果啊!”
孙二孬说:“这小子走的不是绿色通道,而是绿色高速公路!”
胡万有说:“岂止是绿色高速公路,依我看,是绿色飞机!”
刘臭蛋说:“你们形容得都不对,应该坐的是绿色长二捆!”
元叔布满皱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此时,老泪纵横。
说到“长二捆”火箭的时候,孙丫丫抢过话头说:“你们不说我都忘了,快打开电视,国家又要发射‘神六’了!”
众人急忙打开刘臭蛋的背投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正在重播关于“神舟六号”发射成功的新闻,播音员兴奋激动的话音在屋子里环绕激荡着,振奋人心。一屋子人敛声静气,紧紧地盯着屏幕,只见“神舟六号”在总指挥的一声“点火”命令下,向下喷出一阵红色浓烟,腾空升起,直插九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