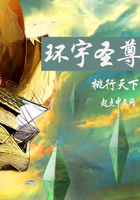“生”于1977
一个时代怎样开始,一个时代就怎样结束。
仿若十年前《人民日报》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告了“文革”的开始,1977年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消息:取消大学推荐制,全面恢复高考。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这个消息的爆出看似突然,其实已经酝酿了数年,它的出炉和一个大人物密切相关——邓小平。伴随着7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命运的起起伏伏,他的“三上三下”也牵涉着中国知识青年们的命运变迁。1977年夏天,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场从8月13日到9月25日,持续44天的会议充满了争鸣的火药气息,其焦点就是要不要保留推荐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刚刚复出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关键时刻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是,就有了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的这则爆炸性的消息。
这个消息好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当远在新疆的王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还是乌鲁木齐县一个公社的下乡知青。作为1976年毕业的高中生,他和当时广大的知识青年一样选择了到农村插队。
王政:在乡下,磨地都是晚上磨,坐在拖拉机上在那里耙地,尘土特别大,所以人就留两个眼睛,用布把脸都蒙上,灰尘特别大,一般一干就是一晚上,把高的土坡磨下去,在那儿干了一茬子,这一茬子也就算是一季了,把这个干好了以后才能播种,将一百多斤的麦子背着走到地里头,送到播种机上,再扶着播种机开。冬天就是挖渠,一榔头下去一个白点,挖渠完了淘粪,到厕所里打粪便的冰块,因为冬天粪便就像水柱子一样,我们把它打掉,再把它运的地里头,是这样一个过程。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投进水面的一颗巨大的石头,搅动了青年王政平静的心湖。为了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特意购买了茶叶、方块糖等少数民族极缺的东西,找到维吾尔族生产队长,队长很照顾王政,就安排他做了一项清闲些的工作——放羊。
王政:在山上放牧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放牧前,我都要带着一个行军水壶,但很快就喝完了,开始只有强忍着,后来有了诀窍:就是要想方设法抓有奶的母山羊,并将羊奶挤在自带的水壶中,以此解渴。也正是放牧使我有了时间和精力读书、学习。
为了抢时间学习,知青们的智慧真是“可歌可泣”。在新疆长大的75届高中生刘新荣也曾经是公社里的牧羊人,也是利用这种公私兼顾的方式,拼命温习着中学的课本。
因为1977年高考10月份宣布恢复,12月就开考,所以留给考生们的复习时间非常短暂。刹那间,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
1977年,乔保平已经是兰州师范的一名干部,在校办厂任车间副主任。为了复习好文科生都发憷的数学,他专门请了20天假,光数学复习就用去了半个月。他找来几册弟弟中学用过的课本,在自己装订的政治学习笔记本里,把所有的例题似懂非懂地抄写了一遍,还请本校的数学老教师孙金铭重点辅导过几次,并工工整整地在封皮写上了“数学复习笔记”。历史和地理只复习了5天,语文来不及复习就上了考场。
当时,社会上有一句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复习好数学,对于每一位准备高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数学课本的问题,黑龙江双鸭山矿建公司工人胡立德从自家装煤的仓房中找到了一本老教材。
胡立德:自己文科有点基础,就选择了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地理这些科目,根据复习材料,自己基本可以搞定。最要命的是高中数学课本,如果没有老师讲解,单凭自己看,根本看不懂。家境贫寒,也没钱请老师辅导。好在我比较喜欢书,不管什么书,是书我就留着。我在装煤的仓房里发现有一本哈尔滨教育学院1964年编印的《高中数学》。这是一本函授教材,函授以自学为主,考虑到自学的需要,教材对例题的各个步骤就展示得特别详细。每天吃完晚饭,按照教材的顺序,我慢慢啃起来,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学。
复习第一,政治第二,这是程老汉的玩法。1977年秋天,程鹤麟还没成为程老汉,20岁,刚从地处南平市的一座隶属于福建省广播事业局的电台转发台调到福州,任省电视台值机员。局机关就把他们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年轻人留在局机关,负责监管“清查对象”。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程鹤麟的耳朵里,他立马和自己负责监管的对象——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老李谈了一次话:
程:我想去听辅导课,你不会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会,我问心无愧我跑什么?
程:你不会自杀吧?
李:不会,我清清白白不会自杀。
得,小程听课去了,放任老李一个人爱咋地咋地。老李够意思,没逃跑,没自杀,乖乖待在那间小屋里听收音机看报纸,等着年轻的程鹤麟听完课“回家”。
与“文革”期间正常高中毕业、基础较好的的学生不同,任金州的备考之路进行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1977年,任金州已经走过了五年军队、五年工厂的历程。1974年,他从北京电影机械厂转到了厂所属的技工学校担任班主任,兼政治课教师。
任金州:当时大中小学校万马齐喑,谁都不愿意当老师,“臭老九”待遇,知识分子是非常压抑的。我想学习,上大学不成,我通过当老师可以学习,所以只有我去了。教完政治课之后,我就改变了身份,改做学生,坐在最后一排,和技校学生一起学习数学和物理。授课老师们也希望我去听课,因为我是班主任,可以帮助他压阵。就这样,技校两年我把初中到高中六年的课程全补了。上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想,当时心中始终有一个情结:一定要上大学。
大学,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而当报考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时,对当时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更是一个既陌生又奢侈的名词。因为当时的国人很少有接触照相机的机会。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一台相机,海鸥四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元钱的他,是个大花销。献血的钱攒了三年,加上点母亲的资助才圆了他拥有照相机的梦想。说到普通人家与摄影的关系,作家方希打了个比喻:上世纪70年代拍照是件大事,借个相机,换上衣裳,拖家带口奔公园拍一天,跟今天去欧洲旅游一趟差不多。
在197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选择“北京广播学院”这个艺术类院校,选择“新闻摄影”这个专业的考生注定会有那么几分不同。无论是任金州的“热爱摄影这门技艺”,岑传理的“宣传真理,传播知识”,刘建新的“爱玩相机”,还是程鹤麟的“摄影好拉风”等各个版本对于“摄影”的初认知,77摄影班同学到底共同拥有哪些先天特质?任金州班长的话一言以蔽之:与77级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相比,在进入这个专业大门之前,他们已经是一群“出身较好,知识面广,视野开阔”的人。
进入一个非凡的专业,必定经受一番非凡的折腾。与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对于当年录取的学生还要进行一轮特别的考核——专业面试。
刘建新:当时就在四川招一个,报名的就是好几千人,光我那天面试就好几百人。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就进了四川广播局的院子,一抬头看见迎门墙上书写着标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结果考试时考官就问了我:你知道毛主席给广播事业的题词是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考官很满意。到了图片分析这一环节,因为我很早就接触摄影,自己也深爱摄影,所以很自信地对一幅林县红旗渠铁姑娘队人物特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考官们也很满意。面试完毕,双方感觉都不错。
因为摄影专业对考生视力有特别要求,那就是裸眼视力必须1.2以上。广西壮族考生黄著诚小时候因打石头仗,把右眼打伤,视力只剩下0.8,另一只视力尚好。为了抓住难得的高考机会,他硬是把视力表上0.8至1.5的几行“E”的方向全记了下来,忐忑中过了面试。有一天,正在工地干泥水工的他忽然接到通知,招生办找他有事。
黄著诚:我一听差点没从墙上掉下来,心想八成是被招生办看出破绽来了,一路上失魂落魄,硬着头皮回去等待发落。我一进屋就觉得气氛紧张,其中一位北方模样的人眼光特别犀利地盯着我,他先是翻开一本画报,让我评说几幅照片,最后把一张报纸按在墙上,让我离远一点念报上的文章给他听,好在我的另一只眼视力超群,很轻松就念下来了。客人没说什么就走了,这不就更酷、更深不可测了吗?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广院的录取通知书,并且是对视力要求像飞行员一样高的摄影专业。
黄著诚的背表秘笈任金州也用过。当时任金州的左眼1.2,右眼1.0,面对考官叶家铮老师,心中有些紧张,但依靠过人的记忆力顺利通过了视力测试。
任金州:回到单位里,我的心里有点忐忑,我那时候知道学校地址,就给学校写了一个信:北京广播学院招生领导,我实事求是地讲,我的眼睛只有1.0和1.2,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在考试的时候,我就背下来了后两排,结果我的测试成绩是1.5,实际我眼睛没1.5,但是我很喜欢摄影。如果你们认为我1.2和1.0可以上这个学的话,就录取我吧;如果觉得不能录取,我希望你们迅速把我的档案投放到下一个档。
据说,当时这封信转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矫广礼那里,他当场表态说:就凭诚实这一点,录他了。从此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入学视力要求也改为双眼裸视1.0。
一步步走近北京广播学院,对乔保平来说纯属偶然。初始报志愿时他填写了三个学校: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当他向在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工作的姑妈说起报考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离家乡近方便探望照顾祖母时,姑妈非常欣慰,并向他建议再报一所北京的高校,这个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其中有个摄影专业当年在甘肃有一名招生指标。
乔保平: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广播学院的名字,但我听从了姑妈的建议,决定去改志愿。我愣是跑到区招办,调出来报名表把第三志愿划掉,在第一志愿后面加了北京广播学院,以此作为第二志愿。
高考之后,北京广播学院优先招生,乔保平被提前录取。78年元旦过后不久,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兰州师范学校。这时,离学校放寒假的日子很近了。乔保平就赶紧办各种手续,办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很快就回了河北老家与奶奶以及女朋友团聚去了。春节过后,按照开学的日期,乔保平从老家又直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报到。
暑假期间,乔保平返回兰州师范看望同事,学校政工组组长向已经是北京广播学院大一新生的他告诉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你走后,单位又收到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原来春节前后,就在乔保平离开兰州的日子里,其他大学正常录取开始,招办也许忘记了在登记册上划掉他的名字或做备注,兰州大学招生人员翻名册一看,这个考生报了兰州大学没人录,就这样又把他重复录取了。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只是就那么几日,便注定了乔保平同学与北京广播学院有缘而不是兰州大学。
阴错阳差,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只是就那么几日,便注定了乔保平同学与兰州大学终是无缘。
在77摄影班的群体里,有两名女生特别引人瞩目,她们的加盟也颇具戏剧性。一个是有警察背景的福建姑娘温化平,高考分数可以直达北大,但就因为北京广播学院提前录取,她没有经过面试,就被爱才的任远老师直接截留了下来;另一个是在北京郊区某小学任数学老师的王桂华,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被系领导作为“农民生”招进了77摄影班,以表明考试的公正与平等。
1977年冬季高考,570万人激情参考,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录取比例达29∶1。这一年被后来的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当然,它更是许多个人命运重生的拐点,它给予知识和知识分子以应有的尊严和地位,重启的是一个国家走向复兴的伟大梦想。
自此,一众来自四面八方,背景五花八门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踏进了同一个门槛——大学,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骄子。